要闻
-
2025丹霞杯扑克大赛即将登陆韶关 德信竞技助力小城...
10月8日,2025丹霞杯扑克大赛将在广东省韶关市盛大开赛。这项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德信竞技等智力竞技品牌协办的赛事,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智力扑克高手和爱好者同场角逐,为这座以自然风光闻名的岭...
-
Telesin泰迅推出DJI OSMO 360全景相机专用延长杆 ...
大疆(DJI)最新发布的 OSMO 360全景相机以其强大的影像能力和便携性迅速成为内容创作者的宠儿。然而,想要充分发挥这款相机的潜力,合适的配件至关重要。Telesin泰迅迅速响应市场需求,推出的可延长杆等兼容配件...
-
自有逸致,悦聚环宇丨惠州中海环宇天地招商启动会...
自有逸致,悦聚环宇!2023年8月4日, 惠州中海广场丨环宇天地项目招商启动会暨首批品牌商户签约仪式盛大召开。 招商启动会正式开始前,惠州市商务局领导与部分品牌商户代表,就惠州商业市场情况及商业投资环境...
作家梁鸿:在父亲坟前感受到逝者的生命力
发布时间:2020/04/12 要闻 浏览:510
清明节前,作家梁鸿出版了和“亡者”相关的长篇小说《四象》。这是梁鸿的第三本虚构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活人和三个亡灵的“奇幻漂流”。活着的人是IT精英韩孝先,三个逝者亡灵分别是基督教长老韩立挺、留洋武官韩立阁、熟知植物的女孩灵子。小说通篇由这四个人的自白构成

梁鸿最初是因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描写农村的非虚构作品而被读者所熟悉。此后,她相继出版《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虚构作品
不久之前,梁鸿本色出演的贾樟柯新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并有望在国内上映。电影讲述的是1949年以来的乡村记忆,梁鸿、贾平凹和余华是电影中的主要叙述者
清明假期,梁鸿接受了专访,谈及新小说、逝者、疫情、新电影和故乡
关于新书《四象》:
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
草地:这本书不像您之前写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像《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虚构作品有个清新的脉络。这本书是四个人的自白,内容上虚幻与现实相结合,表达也很跳跃,容易造成阅读上的滞重,该如何更好地把握这本书内容?
梁鸿:这本书是四个人物轮流说,确实容易有滞重感。但是同时,你也会觉得非常耐咀嚼,如果反复读的话,会发现其中有意思的地方。在这本书里,地下的三个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幽闭,当他们再次出现在人世间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有表达欲的,他们说的话,都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和他所期望的一个状态。
草地:《四象》这本小说的书名怎么理解?
梁鸿:“四象”有多重意义。韩孝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多重人格,他分裂成了他早前听说过的那三个人(在书中,父亲曾经给他讲过这三个人及他们的故事)。后来发现在写作上不大好操作,所以让韩孝先看到其他三个,后来一起来到人世间。在村庄、城市行走,他们是在对话,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四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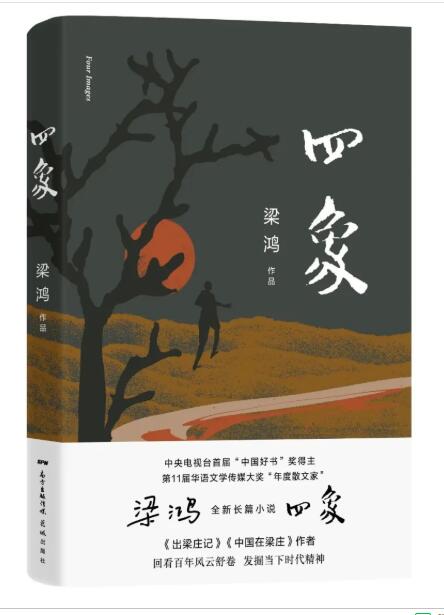
梁鸿 / 花城出版社 / 2020
当然,“四象”还包含着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这种自然的循环在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哲学思想。
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一个人的四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是独立的人格,这些人格合在一起,可能就昭示着这个世界的不同层面。在小说里,他们一起走出墓地,走到县城、省城,那个曾经是高考状元和IT精英的年轻人成了大师,接受人们狂热的崇拜。但同时,他发现,他只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甚至是工具,人们的欲望难以填满,甚至想超越生死的界线。所以小说的最后,孝先放弃人间的一切,回到墓地。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三个人的声音,世界又回到了原来的秩序里面。即使这种秩序并不完美。
草地:这本书里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意象,比如绿狮子、血月亮。这些意象该如何理解?
梁鸿:“绿狮子”是在地下的韩立阁年复一年看着大河对面那些疯狂生长的野草产生的意象。不断生长的野草,就像一头威武的狮子一样,翻山越岭而来,离村庄越来越近。而韩立阁非常害怕那头狮子跨到河的这边,把他身后的村庄淹没掉,因为他的仇还没报。当宽阔河岸对面那些郁郁葱葱的植物过分茂盛时,就代表着某种压迫性的力量。我想,对于在地底下躺了整整一甲子的韩立阁而言,这既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也是一种心理的变化。当他看到那种野草在生长、大地荒芜的画面时,就是植物要占领世界的感觉。
至于“血月亮”,我记得2019年有两次月全食,当看到月亮变得血红时,相信人们都会震撼。虽然“血月亮”背后的科学原理,大家容易理解,但依然心存敬畏。所以我把现实拿过来,化用在小说中。
草地:您在后记里说,写这本书最初的冲动是想把父亲墓地里“听到”的声音写出来。这本书是如何从最初的一个冲动,几经修改,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梁鸿:这是挺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个冲动、意向并不足以支撑你写成一本书。当你想到这块墓地的时候,那里边的人,都有历史;你原来村庄里边的人也都有历史,所以写作时就会自然而然把这些结合起来。有了具体的声音、具体的人就好写了。
比如,当我想到三个墓地里的声音时,首先想到的是灵子。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原型,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夏天喝了凉水,突然间就死掉了,当时我才小学三四年级。死掉之后就埋在我母亲坟边,从来没有人去扫过墓。有时候我们去为母亲上坟,踩到她的坟,几乎已经是一片平地,很难察觉了。父亲告诉我,“不要踩,这是一座坟,里面埋着别人家的闺女”。
写作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这个无名的女孩。感觉她永远被遗忘了,被她的家人、被我们、被世间遗忘。所以我特别希望赋予她声音。这个具体的人物就出现了,慢慢从只有骨干,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另外一个人物韩立阁,是我们村一个大家族里当过官的人。《中国在梁庄》里面写到过他,但只写了一点点。在《四象》里我把他又丰富化、血肉化了,又虚构了一些东西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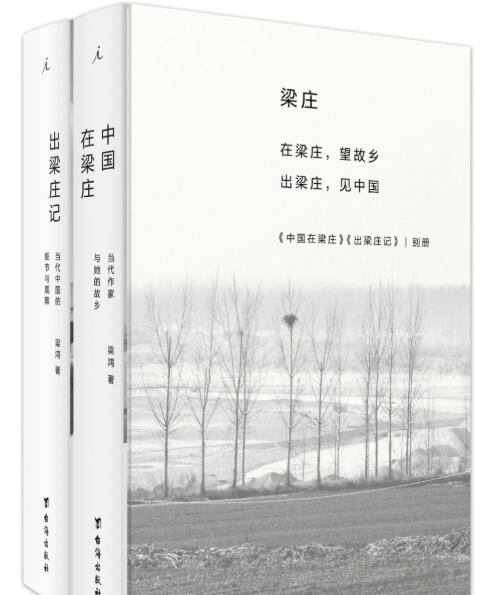
梁鸿 / 台海出版社 / 2016
包括韩立挺。我们村确实有这样一个长者,活得时间非常长,一辈子德高望重,我们对他都像对神一样地恭敬,后来他去世了也埋在墓地里边。
当我想到这几人的时候,慢慢这本书的框架就出来了。从那些最初星星点点,慢慢变成一片草原,或者说像一棵树一样有机地生长在一起。
草地:《四象》这本书的腰封上,描述这是您写作以来最有冲动也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
梁鸿:因为我母亲去世很早,所以我年复一年在墓地里面来来往往。可能会对坟墓、死亡更加敏感。上坟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谈起里面的亲人。当你在坟头谈论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仍在活着。
这种感觉其实对乡村而言可能更加明显,但也不是说城市就没有。因为乡村和大地相关,跟原野相关,坟头又在原野之中,你的生活也在原野之中,所以乡村一直处于一种特别自然的环境中。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我特别着迷的一点。
乡村的孩子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的生和死是在一起的,村庄前面是活的人,村庄后面是去世的人。所以说生与死从来都是在一起的,处于一个没有完全割裂的状态。
所以,当我在父亲坟前时,突然就感受到了逝者的那种生命力,依然顽强地影响着活着的人,这是我特别有冲动想写的。
为什么又很压抑?因为写一个地下之人,真的很难。他要干吗?他想干吗?你想让他干吗?你想让那几个人来表达出他本来的自我,他们都在地下躺着几十年了,他们该怎么表达自己?你得想象。

比如韩立阁这样一个190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留过学,回来从政,倡导革新,大时代都经历过,但最终那么一刀,他的命就没了。他自己会怎么想他的命运?你得替他设想。
至于“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我很喜欢这句话。他们在地下孤独地躺着,希望被发现,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倾听。类似于亲人在暗夜相逢一样,找到了同路人,找到那种情感。所以我想暗夜之中这三个人(韩立阁、韩立挺、灵子)一直在等待,等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等到韩孝先这样一个人,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携带着各自的记忆,携带着各自的痛苦和渴望。
其实写这些想表达的还是现在的一种精神状态。现实中一种很荒诞的存在,现代秩序的失控,或者说灵魂的虚空。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我书里也写到,当韩孝先成为“大师”后,每个人对他都特别恭敬。难道人们不知道韩孝先是假的吗?难道就那么愚昧,真觉得来了一个上帝、一个大师?但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慰藉,所以才造成整体的一种荒诞。最后韩孝先被关了起来,变成一个被观赏的大师,这也是特别荒诞的一种行为,也恰恰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种表征。
草地:《四象》这本书在您的村庄书写系列中处在什么位置?
梁鸿:这本书依然是梁庄故事的一部分,但又不只是梁庄的故事。尽管这本书可能里边有亡灵、有精神病人、有癫狂的语言,但我最终目的还是想表达现实,想传达我对现实的感受。
关于写作
乡村写作不可能穷尽,得看有心人
草地:虚构与非虚构,您更喜欢哪种表达方式?
梁鸿:很难说我更喜欢哪一个。虚构和非虚构对我而言,更多的是根据题材和需要来选择。比如《四象》,因为我一开始想的就是那样一个意向,所以自然就是小说。如果采取非虚构的方式,就没法写,因为地下的人怎么可能说话?再比如《中国在梁庄》,我一开始就想一个真实的村庄,所以自然就是非虚构写法。
包括《梁光正的光》这本小说,我觉得这样一个虚拟的父亲,可能是所有人的父亲,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他的那种永远无法照亮别人的光。如果是非虚构的写法,比如写我自己的父亲,可能就有很多绑手绑脚的束缚了。所以这时候只能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如果有一天,我想写我真实的家庭,那我一定得老老实实按照一个非虚构的框架来写。

梁鸿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7
草地:对于中国乡村的书写已经数不胜数了,您觉得乡村书写是否还有可挖掘的余地?
梁鸿: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其实都没有穷尽不穷尽的说法。即使乡村已经消亡了,但是乡村所塑造和影响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消亡。最起码,乡村作为人类经验之一并没有消亡。
我也并不觉得调查类的乡村写作,或者说这种非虚构的写法就已经穷尽了,就看有没有好的作者。那么一个庞大的,几千年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环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穷尽了?我觉得以后肯定还会有好的作品出来,得看作家怎么去琢磨。
草地:就乡村写作这一方面,您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梁鸿:其实我的写作比较杂,我自己看人类学、社会学的作品比较多,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等人类学著作,也有历史学方面的如《叫魂》,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等等。当面对一个真实的乡村时,想的是所面对的场景,而不是该用什么方法来写,用谁的方法来写。我的乡村写作肯定受了很多很多前辈的影响,他们多多少少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影响我。如果说受谁的影响最深,一下子还想不出来,但我吸取了很多前辈的经验。

关于疫情
疫情会导致文明秩序的深远改变
草地:能不能谈谈您疫情期间的思考?
梁鸿:我想,在这样一个疯狂的病毒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亲历者,不管你在武汉、北京,还是意大利、法国,不管你是得没得这个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迫隔离了。这种隔离长达两个月,甚至以后还要继续,孩子也没办法上学,正常的工作和交际没有了,娱乐形式全变了,等等。我们都应该借此去反思一下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问题和出路。
更具体而言,我们要反思自身,这样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否则这场灾难过去就过去了,可能半年大家就会忘了,又该吃吃该喝喝。那么,这一场大的灾难,就成了往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好的可能,但也是最可能的可能。
草地:如何看待疫情带来的“社会突变”?
梁鸿:这次的疫情其实是整个世界大秩序的改变,包括我们的生产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村与村的关系。
我们看到,疫情暴发时,村与村之间联通的路被挖开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文明倒退,但是每个人都好像觉得特别理所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又一次变得非常牢固,你要保持一点五米以外,如果你没有戴口罩,你就是我的敌人。
疫情也会改变世界格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在抢口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
这些改变短期内可能是经济形态或制度形态的变化,但更深远的是文明秩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至于最后改成什么,还要拭目以待。
草地:之前您在微博上说,三年前写这本书(《四象》)时,没想到世界如此变化,细想竟有些心惊,韩孝先的暴怒和世界的荒谬逐一呈现。
梁鸿:确实有这种感受。这段时间我突然想到这本书,好像世界就是以如此暴虐的方式来让人类反思,不管是以病毒的方式,还是用其他方式,让大家看到问题,反思自身,反思文明的形态。
关于电影:
看到破败老屋时,特别羞愧
草地:您去年5月参与拍摄贾樟柯的新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第一次触电是什么感觉?同样都是围绕村庄,文字和影像记录有何差别?
梁鸿:通过影像,能重新反观自己的村庄,也是挺有意思的。拍摄时,我又回到老家。我们家的老房子已经非常破败了,当时我特别羞愧,觉得这房子真应该修修了。见到老房子的一刹那其实特别不好意思,当然我也没给贾导说这个事情。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我让自己认识的老屋变成这样,这是我父亲的家,我童年、少年生活过的家。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预告片
修这个房子其实是我父亲一个非常大的愿望。因为那是他的家,是他拼了命才保住的家,是他生命和所有价值的体现。
但对我而言,我觉得修房子太虚荣了,人都在外面,又不怎么住。所以我一直没有修,一直排斥这个事情,也一直没有回应父亲时不时流露出的愿望。然后,他就去世了。
我的姐姐们也提过这个事情,我也没太在意。这个影像使我突然间从别人的眼光来看房子,它确实是太破败了。会发觉原来我对家是那么漫不经心,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拍摄中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我觉得视觉创作和文字创作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文字表达更内化一点,而影像有一个全景观。另外我觉得影像有导演的个人意志贯穿其中,导演必须是一位指挥若定、胸有成竹的将军,否则,没办法既控制又脱离那巨大的工作团队,没办法实现自己独立的思想。贾导背后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协调这支队伍很难,我就做不来,还是老老实实一个人写字。
关于故乡:
故乡给你的爱恨交织,是很珍贵的
草地:您每年要回几次梁庄?
梁鸿:今年还没回去,以前一年至少两三次。
草地:很多乡村写作者都和乡村有一些利害关系,这种现实会不会让您在写作时感到为难?
梁鸿:这个还挺复杂的。回到家乡的感觉并不都是愉快的,说实话有时各种人情世故,也让人非常灰心丧气。一方面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已成为过客。其实反过来想,大家都在认真养活自己的孩子,认真努力地生活,不对吗?
故乡对于我们这些离开家的人而言,可以提供反思生活的特别重要的视角。对于家乡的感情可以用爱恨交织来表达,但爱恨交织里面,也是因为爱才产生那些难过,才会觉得灰心丧气。
人离开故乡,会重新反观自己的生活,会更加努力。也只有故乡才能给你带来这些思绪,观看其他任何风景都不会有的。有些地方是很美,但它不会让你五味杂陈。
所以我觉得故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不能简单地评判。不管失望也罢,灰心丧气也罢,难过也罢,这都是故乡给予你的非常重要的情感。
草地:前不久您修订出版了《神圣家族》,写的是小镇里的群体命运。从最初的《中国在梁庄》“在乡村里看中国”,再到《神圣家族》“在小镇看中国”,两个视角有何不同?
梁鸿: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小镇和乡村不像城市和乡村之间有截然不同的形态。小镇上有一些经商的人,但大部分都还是农民,在小镇周边都有自己的土地。小镇大部分是由乡村的集市慢慢发展而来的,所以小镇和乡村之间是连续的,它不是一个断裂的、二元对立的产物。

梁鸿 / 中信出版集团 / 2020
草地:此前您教儿子学河南话,成功了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梁鸿:他不排斥学河南话,只是说得不好。因为他常年在北京,说河南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对他而言,就是个北京的孩子,但是他母亲的老家是梁庄,他也经常跟母亲一块回家去玩,对于梁庄,他会有一个记忆。
草地:您写了这么多乡村社会的荒诞,那您理想中的乡村是什么样的?
梁鸿:我说过从来没有桃花源的村庄。理想乡村是什么,这个我真是回答不出来。
上一篇: 不妨让直播成为复工“加速键”
下一篇: 机构:长三角区域楼市销量快速回升



